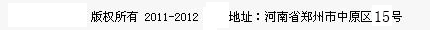近十多年来,我国实际工资增长率持续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种现象不仅和我国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历史情况不符,也和经典的新古典理论相悖,值得深入研究。本期为大家带来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吕光明教授和李莹博士的《我国工资超劳动生产率增长背后的故事——基于省份面板模型的经验分析》,本文原载于年第3期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引言
工资和劳动生产率是国民经济运行中反映劳动者投入与生产贡献之间关系的一对变量,也是经济学研究中备受的一大主题。经典的新古典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信息充分、生产组织方式不变等完美假设条件下,处于均衡状态时劳动要素的价格即工资等于边际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比例关系应基本稳定,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应基本一致。
然而,观察我国实际工资增长率和人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变化可以发现:二者关系在年前后发生明显变化,前者在年前的多数年份都低于后者,而在年后绝大多数年份则超过后者。
本文首先纳入相对生产率、劳动力供给、劳动力转移、投资规模占比与投资结构三类五大结构因素,搭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非一致性变动分析框架,然后采集-年我国31个省份数据构建省份面板模型,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定量揭示工资超劳动生产率增长背后的结构诱因及其驱动机理。
结构分析框架
(一)基本模型
假定生产函数是Cobb-Douglas形式,且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则有:
式中,Y为产出,A为技术进步,L为劳动投入,K为资本投入,α和β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劳动的实际价格(工资水平)由劳动的边际产出决定:
式中,w为工资水平,MPL和y分别为边际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在趋于均衡的经济体中,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收入份额)基本保持不变,表明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是同比例变动的,即两者的增长应该具有一致性。
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一致增长结论的得出是需要严格的近似于完美的市场条件。然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市场化改革和结构转型进程中的国家,一些结构冲击因素会引致工资与劳动生产率非一致增长,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三个类别,具体是:一方面,劳动生产率行业差异与工资水平行业趋同之间的矛盾会引发全社会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非一致增长。另一方面,投入要素供给和需求状况的变化也会引发劳动的供需不均衡以及要素边际产出递减,进而也会引致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出现增长非一致性。在我国现阶段,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弱,另一类是资本要素投入对劳动力引致需求的变动。上述三类结构因素引致工资与劳动生产率非一致性变动的作用机理是:
1、相对生产率变动的巴萨效应
巴萨效应假说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传递过程,且有严格假定条件。其中最核心的一步是:在资本回报既定的条件下,可贸易部门相对于不可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可贸易部门工资水平的提高。若劳动力可以跨部门自由流动,那么工资差别必然引起劳动力自低工资的不可贸易部门向高工资的可贸易部门流动,不可贸易部门为吸引劳动力而提高工资水平,进而导致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提高。本文将其称之为产业部门间的“工资水平溢价”。
2、劳动力供给冲击的效应
人口红利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之一,而如今劳动适龄人口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两个层面的红利都在逐渐消失,劳动力供给冲击驱动了工资超增长。
3、资本投资冲击的效应
投资规模占比变动对工资的影响与劳动力供给状态紧密相关。除投资规模外,投资结构也会对工资产生巨大的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到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2所示:
(二)省际面板模型及数据说明
1、省份面板模型说明
为反映劳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的长期关系,对式(2)两侧取对数,并进一步构建如下的省份面板数据模型:
出于数据连续性考虑,被解释变量的工资水平选择“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作为代理变量,具体采用对数形式即lnw;解释变量劳动生产率选择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代理变量,工资和劳动生产率采用对数形式以纠正分布的非对称性;考虑到工资调整的滞后性以及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可能的反向因果,解释变量采用现有研究的常见做法,即滞后一期的对数形式lnyi,t-1,以减弱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回归系数β1的含义是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即劳动生产率提高1%后导致工资提高的百分比。
为了考察结构因素对劳动工资的影响,这里在基准面板数据模型基础上纳入结构因素及控制变量,其形式如下:
与劳动生产率类似,结构因素和控制变量也均采用一阶滞后形式以减弱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偏误。
鉴于我国结构转型的渐进性,为反映结构因素和劳动生产率对工资影响随时间推移的变动趋势,我们在式(6)基础上分别加入结构因素与时间的交乘项以及劳动生产率与时间的交乘项,分别得到式(7)和式(8):
2、结构因素的变量选择说明
根据前述相关理论,本文的结构因素依次选择反映巴萨效应工资传导机制的相对生产率变量、反映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转移的变量、反映投资规模占比及其内部结构的变量。
(1)相对生产率变量
本文将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相对生产率(rprod)作为检验追赶型经济体巴萨效应的代理变量,具体采用对数形式。通常认为制造业和服务业是最接近可贸易与不可贸易部门定义的行业,但受制于省份制造业数据不连续性,本文选择第二产业代表可贸易部门。
(2)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转移冲击变量
劳动力供给(labor)用劳动适龄人口占比来衡量,具体为16-6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劳动适龄人口占比越高,表明直接的劳动供给越充足。劳动力转移(urban)用城镇化水平来衡量,即城镇常住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城镇化水平越高,表明本地区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少。
(3)投资规模占比与投资结构变量
投资规模占比(invrt)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在GDP中的占比来衡量,投资规模占比反映一个社会或地区对资本的依赖程度。投资结构(invstr)采用民间投资占比作为代理变量。
本文基于-年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样本进行分析。其中,民间投资数据来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和中经专网。
省份面板模型全国总体层面的估计分析
(一)结构因素和劳动生产率对工资影响的估计分析
首先在结构因素纳入前对式(5)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见表2第(1)列。可以看出: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为0.,表明劳动生产率提高1%导致工资增长0.3%。
在纳入结构因素后对式(6)进行估计,得到结果见表2第(2)列。可以看出:工资对劳动生产率的弹性系数下降到0.,幅度在40%以上。同时,三类五大结构因素均显著影响工资水平,表明结构因素极大地驱动了我国工资水平的超劳动生产率增长。
(二)结构因素和劳动生产率对工资影响的变动趋势分析
结构因素和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影响并非一成不变。为考察二者对工资影响随时间的变动趋势,借助式(7)和(8)得到如表2第(3)-(8)列所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首先,相对生产率与时间交乘项系数为-0.,经济意义很小,且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其次,从促进劳动力需求的投资视角来看,加入投资规模占比与时间的交乘项后,投资规模占比的低次项系数增大到0.,而投资规模占比与时间的交乘项系数为-0.,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年间,投资规模占比扩大对工资超增长的拉动效应是逐年递减的,而这可能是投资的就业效应在减小。最后,从劳动力供给来看,加入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与时间的交乘项后,低次项的系数绝对值略有提高,但交乘项系数很小,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省份面板模型地区层面的估计分析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着很大的阶段差异,将31个省市自治区划分为三个地区后借助式(5)和(6)进行回归估计,得到的结果见表3。
(一)东部地区省份面板模型的估计分析
相对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巴萨效应以及潜在劳动供给总量的减少、劳动力转移程度加深是驱动东部地区工资超增长的结构诱因。
(二)中部地区省份面板模型的估计分析
投资规模占比扩大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增加是中部地区工资超增长的结构诱因。
(三)中部地区省份面板模型的估计分析
尽管西部地区工资也受到了投资规模占比、劳动力供给以及劳动力转移等结构因素的显著驱动,但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正常增长相比,这些驱动作用带来的超增长要小得多。
(四)对结构因素估计结果地区差异的进一步讨论
1、相对生产率估计系数的地区差异
巴萨效应工资传导机制仅在东部地区成立,而在中西部地区不成立,可能原因是:第一,过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会抑制工资水平的超增长。第二,劳动力市场分割会抑制巴萨效应工资机制的传导。
2、投资规模占比与投资结构估计系数的地区差异
从投资规模占比的回归系数来看,投资规模占比扩大对工资超增长的驱动作用大小关系为中部>西部>东部,这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时期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密切相关。
3、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转移估计系数的地区差异
以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代表的劳动力供给对东部和西部工资超增长的驱动作用较为显著,但对中部地区工资超增长的驱动作用不够显著。
结论与启示
在完美的假定条件下,工资应该等于边际劳动生产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应该基本一致。然而,自年以来,我国实际工资增长率却呈现出持续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态势。本文首先结合我国的转型背景纳入相对生产率、劳动力供给、劳动力转移、投资规模占比与投资结构三类五大结构因素,搭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非一致性变动分析框架,然后采集-年31个省份数据构建省份面板模型,从全国和地区两个层面定量揭示工资超劳动生产率增长背后的结构诱因及其驱动机理。结果发现:
(1)从全国总体层面来看,结构因素极大地驱动了工资水平的超劳动生产率增长。具体从三类结构因素看,以“工资水平溢价”为核心的巴萨效应工资传导机制在全国层面成立;投资规模占比和民间投资占比每扩大1个百分点分别驱动工资超增长0.和0.个百分点;劳动适龄人口占比每减少1个百分点和以城镇化水平代表的劳动力转移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分别驱动工资超增长0.和0.百分点。
(2)分地区来看,结构因素对工资超增长的驱动作用大小与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差异密切相关。劳动生产率水平越高的地区,结构因素对工资超增长的驱动作用越强,劳动生产率对工资的影响则会相对弱化。具体地,东部地区工资超增长的结构诱因是相对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巴萨效应、劳动力供给和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中部地区工资超增长的结构诱因则是投资规模占比扩大引致的劳动力需求增加;西部地区工资由结构因素驱动的超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正常增长相比要小得多。
文章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本期小编:周建亮
欢迎大家积极投稿,提出宝贵意见,联系邮箱:bnulmrc
.南宁最好的白癜风医院中科让您告别白癜风秀健康